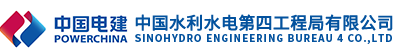大地的詩行 |
|
|
|
|
我們管這叫“定線”。可在我眼里,這哪里是冷冰冰的測量,這分明是寫詩前的“打腹稿”。那亮晶晶的經緯儀,便是我們擰開的第一支鋼筆。我們瞇起一只眼,從目鏡里望出去,世界便被收束成一個小小的、圓圓的視場。視場里,是那些熟悉的、幾乎要被忽略的風景。或許是鄰村那棵歪脖子老槐樹最頂端的枝丫,或許是遠方一座水塔那模糊的圓頂。 現在,它們不再是尋常的景物了,它們成了我們詩句里的一個“韻腳”,一個必須被牢牢釘在大地上的坐標。我們的腳,深深地陷在初春解凍的、油黑發亮的泥濘里,可我們的視線,卻通過這冰涼的儀器,與一個遼遠的、確定的未來緊緊相連。我們一遍遍地校對,調整,仿佛一個詩人,在為一個最妥帖的字眼而反復沉吟。我們丈量的,又何止是兩點之間的距離?我們分明是在丈量著一段舊時光與一個新時代之間的,那看不見的、卻又驚心動魄的尺度。 我們的詩句,最先被那些破土而出的橋墩所吟誦。它們起初是笨拙的、粗野的,帶著大地深處的蠻荒氣息。可很快,它們便一節一節地,向著澄澈的天空生長起來,變得光滑、挺拔,像巨人的手指,又像一列頂天立地的驚嘆號!它們以一種不由分說的、雄壯的姿態,站在了這片原本只屬于麥苗與楊柳的土地上。 那天傍晚,我收工回來,就在離工地不遠處的田埂上,看見了一位老農。我認得他,他就住在附近的村子里,我們都叫他老陳叔。他正牽著他的那頭黃牛,一動不動地站在那里,仰著頭,望著那已初具規模的橋墩出神。夕陽給他的側臉鍍上了一層厚重的、古銅色的光澤,像一尊沉默的雕塑。他的牛,在不耐煩地甩著尾巴,低頭去啃剛冒頭的草芽,可他,卻仿佛被施了定身法。 我走過去,遞上一支煙。他遲緩地回過頭,臉上的皺紋像是干涸土地上的裂璺,深深刻著與這片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的印記。他接過煙,目光又黏著回到了那些龐然大物上。 “叔,在看啥呢?”我問。 他嘬了一口煙,煙霧從他那缺了顆門牙的縫里慢悠悠地溜出來。他并不看我,只指著前方,用一種混合著迷茫與敬畏的語調,喃喃地說:“我在這地里,刨食刨了一輩子啦……從俺爺那輩起,就看慣了這地平線,圓圖圖的,像個碗邊兒。可現在……”他頓了頓,像是在積蓄力氣,“可現在,你們把這大家伙往這一戳,這天,好像都讓它們給支棱起來啦!” 我順著他的目光看去。是啊,那些灰白色的水泥巨柱,在晚霞的映照下,泛著一種溫暖而堅實的光。它們不再是闖入者,倒像是從這片土地里自然生長出的脊梁。 老叔忽然轉過頭,眼里的渾濁被一種新奇的光照亮了,他咧開嘴,憨憨地一笑,問道:“同志,你說……等那長龍一樣的火車,從這‘天路’上嗖地一下飛過去的時候,那聲響,是像打雷呢,還是像刮風?” 我一下子竟被他問住了。我腦海里閃過無數技術參數,卻覺得哪一個也回答不了他這詩一般的問題。我只好笑著搖搖頭。 他也不再追問,自顧自地又抬起頭,伸出他那布滿老繭、像枯樹根一樣的手指,一個一個地,認真地數起了橋墩:“一根,兩根,三根……” 我沒有打擾他。我知道,他數的不是冷冰冰的橋墩。他數的,是他這片沉默的土地上,剛剛長出來的、嶄新的標點符號。這條鋼鐵的詩行,不僅將縮短他與遠方兒女的距離,也正在將他看了一輩子的、那個“圓圖圖的”世界,徹底地打開。 晚風拂過麥田,帶來新泥與青草的香氣。遠處的橋墩靜靜地矗立在暮色里,像一列等待檢閱的士兵,沉靜,而充滿力量。我忽然覺得,我們寫的這首詩,或許在千百年后,會被風雨侵蝕了韻腳,但它那改變山河、聯通人心的氣魄,將會像這大地本身一樣,綿延不絕。這首名為“平漯周”的長詩,正被夕陽烙上金色的印章,而我們每一個人,都是這詩行里,一個幸福的字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