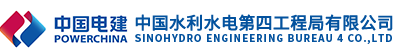重陽壩上風,吹我少年行 |
|
|
|
|
時光的車輪滾滾向前,如今的我已在水電四局扎根多年。在這日復一日的相伴中,每一個項目現場的忙碌身影、每一處水電設施的平穩運轉,都如同歲月長河中的璀璨星辰,鑲嵌在我職業生涯的天空。窗外的秋風裹著桂花香漫進來,當第一片銀杏葉打著旋兒落在窗臺,我忽然意識到——那個登高望遠、插茱萸的重陽節,又悄然爬上了歲月的枝頭。窗外秋風輕拂,帶著絲絲涼意,也勾起了我心底那段深藏已久的回憶。 2010年秋,如一幅細膩的水墨畫,漫過金沙江畔,將向家壩水電站的壩體輕輕暈染。那壩體在陽光下泛著堅實而沉穩的光,仿佛一位沉默卻可靠的守護者。彼時,我背著半舊的雙肩包,懷揣著大學課本與一顆忐忑不安的心,踏上了這片土地,開啟了畢業實習的征程。命運的巧手安排,讓我抵達工地的第三天,便邂逅了重陽節。彼時,壩體主體工程已近收尾,可工地上依舊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。塔吊的長臂在高空靈活擺動,似是巨人在揮舞著有力的臂膀;運輸車在工地道路上往來穿梭,揚起陣陣塵土,奏響一曲忙碌的交響樂;焊機噴出的藍色火花在陽光下格外耀眼,如同夜空中閃爍的星辰。我被分到經營組,跟隨李師傅學習成本核算。李師傅是個資深的老水電人,臉上刻滿了歲月的風霜,每一道皺紋都仿佛在訴說著他與水電事業的不解之緣。他的手里總攥著一本磨破封皮的核算手冊,那里面記錄著他多年的經驗與智慧。“重陽也不能歇,這段時間是材料消耗的關鍵期,今天得把壩體防護材料的用量核清楚。”清晨的薄霧還未完全散盡,李師傅便帶著我匆匆往材料倉庫走去。倉庫里,堆著成垛的防護網和密封膠,空氣中彌漫著淡淡的建材味道。李師傅蹲下身,仔細翻查入庫單據,指尖在紙張上快速滑動,眼神專注而認真。“你看,這里的防護網規格要和壩體結構對應,算多了浪費,算少了不夠用,經營就是要摳細節、守精準。”我捧著筆記本跟在一旁,筆尖飛快滑動,把他說的每一個數據、每一個注意事項都仔細記下,生怕遺漏半點關鍵信息,那認真的模樣,仿佛在記錄著一份無比珍貴的寶藏。 正午時分,食堂的煙囪里飄出陣陣暖意。走進食堂,竟看到餐桌上擺著幾籠熱氣騰騰的重陽糕,還有一壺冒著熱氣的菊花茶。“知道今天重陽,食堂特意給大伙做的,你們這些孩子們也嘗嘗鮮。”大師傅笑著給我遞來一塊糕。軟糯的糕餅入口,帶著淡淡的桂香,那一刻,鄉愁如潮水般涌上心頭。往年此時,我總會和家人圍坐在院子里,吃著奶奶親手蒸的重陽糕,聽爺爺繪聲繪色地講茱萸辟邪的故事。李師傅看出了我的失神,坐在我身邊咬了口糕:“想家啦?我年輕的時候,第一個重陽也在工地上過,那時候條件可比現在差多了。”他指著窗外的大壩,“你看這壩,等建好了,能照亮多少人家?咱們水電人,過節守著工地,就是守著千萬家的團圓。”他從口袋里摸出一小枝曬干的茱萸,塞進我手里,“老家的習俗,插茱萸祈福,你帶著,也算在工地上過了個正經重陽。”那茱萸帶著淡淡的草木香,在秋日里格外暖心。 下午,我們要去壩頂核對防護層施工的面積。順著腳手架往上爬,秋風拂過臉頰,帶著金沙江的濕潤氣息。李師傅走在前面,腳步穩健,時不時回頭叮囑我抓穩扶手。到了壩頂,他指著錯落的壩面結構,一一指出需要重點防護的區域,教我如何根據面積和厚度測算材料用量。我拿著卷尺在壩面上小心挪動,認真記下數據,秋風把筆記本吹得嘩嘩響,李師傅就用身體幫我擋住風。夕陽西下時,我們終于核完最后一組數據,壩頂的風裹著余暉,灑在兩人帶著汗珠卻滿足的臉上。 晚飯過后,項目部的工友們聚在活動室,有人彈起吉他,有人唱起老歌。李師傅給我講起他在各個工地過重陽的故事,從黃河岸邊到金沙江畔,每一個故事里都有堅守與熱忱。我摩挲著手里的茱萸,看著眼前這群可愛的人,忽然覺得這個重陽格外有意義——沒有家人陪伴,卻有師傅的教導、工友的溫暖;沒有登高賞菊,卻在壩頂“登高”望遠,望見了水電事業的厚重與光榮。 實習結束離開時,我把那枝茱萸夾進了專業課本里。如今,多年過去,那本課本早已有些陳舊,但夾在其中的茱萸,依然散發著淡淡的草木香,仿佛時間從未流逝。向家壩那個秋日里的重陽,依舊清晰如昨。李師傅的叮囑、壩頂的秋風、重陽糕的甜香、茱萸的草木味,還有那座在暖陽中拔地而起的大壩,都成了我最珍貴的記憶。 那陣重陽壩上的風,吹走了我的青澀與懵懂,吹醒了我對水電事業的熱愛與擔當,它更像是一根無形的紅線,為我牽起了與水電四局一生的緣分。也讓我明白,真正的成長,往往始于一次難忘的歷練;真正的堅守,藏在每一個平凡卻堅定的日子里。而那個重陽,便是我少年行路上,最溫暖的坐標,指引著我在水電事業的道路上,一路前行,永不停歇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